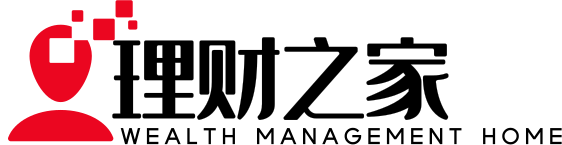上海奉贤环城东路小姐(上海奉贤区小姐一条街)
走不出黑历史的董小姐:请你不要嫌弃我

什么是黑历史?就是有故事的人呗,这年头,保不齐哪个不起眼的女生就是下个“董小姐”。谁还能没点黑历史呢?
1
上初中那会,董妍妍留级插班,和我成了前后座。她体形敦实,头发梳得服帖整齐,鲜亮的衣服映得皮肤黝黑,单眼皮,不苟言笑。
刚开始我们不熟悉,直到数学课她忽然扔给我一团小纸条,里面裹着几个别别扭扭的小字:有好听的磁带吗?
我回:有。民歌。
她转过头,脸上全是惊讶。
课间她低头在桌下听《发如雪》,动情处会握紧我的手杀猪般嚎叫:“你发如雪,凄美的离别,我焚香感动了谁?哦!邀明月……”。她喜欢流行歌,那时,每盘磁带都会附上一个油彩斑斓的歌词簿,董妍妍把歌词抄在软面本上,一笔一划,工整的像小学生的笔迹。
谁的东西找不到了,董妍妍就把整个手臂都伸进那人的桌肚里掏,试卷笔作业本,她都能从“垃圾堆”里扒拉出来。
“贤妻良母啊!”我调侃她。
她脸一红急忙反驳:“你才贤妻良母呢!”黝黑的脸上泛着光亮。
放学后,我们常一起推着半旧的自行车,在南桥和北桥之间来回,桥下面浓烟滚滚的货船逡巡,载满沙石的货船上红旗猎猎飘扬。
“你说10年后我们会干什么?”董妍妍语气怅惘。
“我想环游世界,去很远的地方,然后买一个大房子,一家人住在一起,再养一条小狗,你呢?”
“我啊?我希望我能实现我的理想,想做一个女强人,但不是个愤青。”
她之所以这么说,是因为在刚刚过去的教师教学反馈中,董妍妍很认真地在问卷上写下对每位老师的意见和建议,结果被班主任揪到办公室批评了一下午。
“愤青!不懂得感恩。”班主任是个年纪不大的男老师,推着厚厚的方块眼镜,一脸严肃地教育她。“你看某某,人家成绩第一呢,怎么没写下老师一句坏话?老师们都对你那么好,每天起早贪黑,为你们吃了多少苦?就你不知好歹!”
“所以我要做个女强人,等我有钱了,谁也不会说我是愤青了。”董妍妍握紧拳头。
然而直到毕业了,路修了,桥封了,我们初中时代的理想还沉浸在那些桥梁上。
2
董妍妍的妈妈是个典型的中年家庭妇女,个头不高,一头短发,圆圆的身躯,红彤彤的脸蛋,鞋底抹油般走路飞快,说起话来中气十足。每次去她家玩,她妈妈从不留饭,只在我临走前洪亮如钟地嘱咐她:“好好送你同学!”
第一次去董妍妍家,发现她在家就像是只仓鼠,说话做事总是神色匆匆。下楼时左右瞄下,见空荡荡的没人出来,就快速飞奔下楼。一个染着一头黄发打扮痞气的男生冷不丁就窜出来,忽地对着门猛踹一下,房门前后乒里乓啷响,那是董妍妍的弟弟。见我们吓得缩一下,他就嬉皮笑脸地喊:“黑猪回来啦!”
董妍妍冷漠地扫了眼他,匆匆进屋就反锁门。
有时课间趴到她身上,她就一把推开我,委屈地揉着肩膀说:“别碰我,疼呢!”
“又打架啦?你弟骂你了?”
她点点头,眼神里有了丝怯懦。不久以后,也不见她听磁带了,原来复读机被她弟弟抢走了。
后来,再想见她就没那么容易了。
高中我们不在一个学校,因为住校便断了联络。大学期间,路过几次,我还没进门,她妈妈离得老远就摆手,“出去了,打工去了。”
直到毕业了,有次路过她家的门面房,往常都是嘈杂闹哄的电视声响,这次却安静异常。门市一边的卷闸门已经放下了,另一边半掩着,大厅里货架上的消毒液一瓶瓶摆着,地上汽水瓶塑料罐子捆扎得结实。消毒水刺鼻辣眼,我冲着二楼晾晒衣服的房间喊了一会。
楼上一开始没有动静,后来董妍妍的妈妈披着睡衣下来了,见是我,就懒洋洋地打哈欠,皱着深黑的眼袋,“刚哄睡下小的又被你吵醒了!”
我赶紧表明来意:“阿姨,我是找董妍妍的。”
“不在。”她妈眼皮垂下来,朝门外大路看。
“她去哪儿了?有她手机号吗?”
她妈妈剜了我一眼,不耐烦地快步走动,白眼珠子翻着,“说了不在家!下次来提前约好了!”她手抄裤兜走了,沉重的脚步声在水泥台阶上拖沓。
就这样,我们整整8年都没见过了。
直到我遇到以前的校友,她也是董妍妍远房亲戚。那天,她神秘兮兮地告诉我:“我跟你说啊,我和她(董妍妍)几年不联系了。要不是你问,我都记不得我QQ里还有这么个人。你千万别告诉她是通过我联系上的,不然我跟你绝交!”
“这么夸张?”我惊讶于她试图掩饰的神情。
“以前同学没人联系她,大家不待见她,亲戚也都知道她那点事情,逢年过节都不回,她自己想躲起来你是找不到的。”
“怎么讲?”
她朝我使了个眼色,说:“还不就是她有黑历史呗!”
等我再想追问,她扭头不理会道:“就是有故事的人呗,这年头,保不齐哪个不起眼的女生就是下个‘董小姐’。谁还能没点黑历史呢? ”
“她家里本来就重男轻女,老姨 (董妍妍的妈妈)保守,男女之间不就那么点事嘛!大惊小怪,杀人放火了似的。”说起自己亲眼目睹老姨骂董妍妍的脏话,她表情复杂。
“老姨自己保守的不得了,一大把年纪了活得没意思。她亲妹妹就是我小姨,七八年前新婚当晚就生下大哥,事情当时闹得沸沸扬扬,老姨就愣是几年没理她。”
说到这里,她又换了口气,转念想下说:“不过家里有个丢人的女儿,估计可难受了。藏也藏不住,迟早得见人的啊!”
听了她的话,董妍妍像只仓鼠般,在咚咚的脚步声中飞奔下楼的情景,在我脑海里不断回放。
可我到底还是不知道她有什么黑历史。
3
我终于和董妍妍联络上,并约定周末见面。
她住在南京河西附近,这里房子均价4万一平,走在马路上,高楼把视野挡住了大半。很多楼盘还在捂着,不少投资客坐等涨价,在这么热闹的商圈里找一幢老房子并不难。
见到她,我的第一感觉是她个子没长,还是1米56,额头依旧宽阔,一身纯黑衣裤,小腿和臀部崩得紧紧的,齐腰的黑发毛糙地披散着,单眼皮小眼睛有些浮肿,身形却没有消瘦。
“亲,你够准时的。”她客套地说。
我原本准备好的拥抱和热泪盈眶,在这高浓度的尴尬里,顿时不知往哪儿放。
跟着她进了屋,她介绍说这房子是和4个年轻上班族、一户三口之家合租的。房屋不透风,很哑闷,卫生间里透出一股消毒水的刺鼻味道。董妍妍的房间里也很单调,只有床、柜子、桌椅。东西放得很不整齐,地板上依稀有火锅调料撒落的痕迹。
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。我问她:“你这些年去哪儿了?你妈说你都在外面打工,放假怎么不回呢?”
她才慢慢把前几年的经历一一道来,高中毕业后,她去了无锡电子厂,做操作工,包吃包住再加上省吃俭用,三四年下来也攒了将近8万块钱。后来操作工做够了,她又做过理货员、发单员、推销员,现在则在商场里当服装导购。
除了高中早恋,她还谈了两个男朋友,一个在她醒来后人不见了,她的钱包也不翼而飞了。另一个移情别恋,也离开了她。
董妍妍大腿一拍,说道:“这年头,只有同性才是真爱啊!”说罢翻出最近追看的电子书,津津乐道地介绍霸道总裁和极品小受之间的故事,一本她最为推崇的小说里,含有大量高尺度的意淫桥段。董妍妍啧啧感叹,“这才是纯爱啊!”
“你不做愤青做腐女了。”我说到“愤青”二字的时候,她动容了一秒,便很快继续说下去了。她眼神放光,把手机里的一张图片举过头顶,“这个仰视的角度才叫膜拜啊!”
“既然这样,干脆我俩一起凑合得了。”我调侃。
“NO,NO,NO,我可不喜欢女人,我只喜欢帅哥和帅哥。反正我是不会结婚的,我准备找个帅点的老外一夜情算了。”她半真半假地说,“老外太重口了,不过能混到绿卡就可以移民国外,国外的空气好,福利好,房价还低,简直就是人间天堂!”
董妍妍现在的账户余额不足5000,她抱怨自己离移民国外的目标太远。
她弟弟后来也没上高中就出去打工了,没两年又结了婚,董妍妍一直借钱接济他。结婚、买房、生孩子,现在孩子都三四岁了,还是伸手向她要钱,可是她并不生气。
“他现在是销售主管了呢!”董妍妍一脸自豪。
“那等你结婚了,得让他把钱还给你吧。”
她无奈耸耸肩,说:“谁还我钱都可能,就他不可能的。上面几个姐姐都嫁出去了,就我一人吃饱全家不饿,不问我借问谁借?再说借出去也是要不回来的,就当给家里交了生活费吧。”
她照戒赌吧“老哥”的话说:“借出去的钱是要不回来的,这辈子都要不回来的!”甚至戏谑道:“我弟凭本事借钱,为什么要还?”
“歪理!”我重重地总结。
4
过了段时间,我去董妍妍那儿借宿,她给我腾出半张床。
没一个星期,睡到后半夜,我发现她手机光还亮着,边翻电子书边痴痴地笑,床都一颤一颤的。我问:“你怎么还不睡啊?大晚上熬夜不好啊!”
她甄嬛附体般幽怨地说:“本宫睡眠不规律,一天只能深度睡眠两小时,数羊数星星喝牛奶等方法用尽了,依然不见好转。小主你先睡吧!”
睡不着时,她最常做的事情就是发呆,她能目光呆滞地盯着天花板一个小时一动不动。直到脖子僵硬了,四肢麻木了,她才想起来翻个身。黑暗裹挟中,只有她长长的叹气。
等一早起来,就发现她顶着熊猫眼挂着大眼袋在一旁洗漱了。
快过年了,家里给她安排了一次相亲,相亲对象碰巧出差路过南京,那天她洗了个把小时的澡,直到住在对门的高个子男生憋不住要冲进去了,她才裹着浴巾慢腾腾出来。我拍拍她肩膀鼓励:“加油啊,说不定就遇到了合适的人了呢。”
董妍妍吐吐舌头,“我就是去打个酱油的,不去不给我姐面子。”
结果天没黑,她就灰头土脸地回来了,一屁股坐下就叹气道:“人那么帅,肯定是个gay。”
“瞎说!你怎么知道呢?”
“皮肤那么好,又白又嫩的。”她用力搓自己的脸,照着镜子苦恼地说:“我怎么这么黑啊,我都受不了自己了,怪不得被人嫌弃。”
相亲失败后,董妍妍更加热衷节食减肥了。早饭是一杯微苦的减肥茶,中午晚上都是水果,被饿得脸色蜡黄,嘴唇发白。有时候我看不下去了,递个包子给她,一摸她的手都是冰凉的。“多谢小主了!”她接过包子,佯装请安。
减肥了一段时间,她足足瘦下来六斤。“终于比你轻了!”她高兴地说。周末,我做了米饭炒两个小菜,她看着色香味俱全的饭菜,艰难地动筷子,扒拉碗里的饭菜却咽不下去,干呕了一阵。这时她才察觉胃出了毛病,正常的饭菜也吃不下去了,节食变成了厌食。
5
后来,我陪董妍妍去了几次皮肤医院,她嫌脸上的痘印粉刺太多,让医生开一种调理身体激素的药。“吃了这种药,一年半时间不能受孕,会对胎儿不好。”医生再三强调。
“开吧。”她坚定地说。拿到药后就迫不及待打开吃。
“别吃啊,这种药肯定对身体不好的。”我劝她。她一言不发地往嘴里扔,仰头猛地咕嘟咕嘟灌水。
过完年,董妍妍才回家,待了两天时间就回来了。她脸瘦得颧骨突出,下巴也有尖的轮廓。除了纹眉,她还做了一个半永久妆。
“你就邋遢吧,很快就遭人嫌弃了。”看到我素颜的样子,她不由撇嘴。
她进门第一件事就是翻箱倒柜,把柜子里许久不穿的布鞋都扔了,嘴里碎碎念着,往空了的柜子里塞了十来瓶消毒液。
她沉思道:“有时候我会断片,你懂吗?就是我走到一个地方,突然发现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来这儿了,也不知道这是要去哪儿。”
“那怎么办呢?”
“回到我认识的地方啊,最近我迷迷糊糊地坐上了地铁,下来就在人海堆里走着,某一个时间点我忽然就醒了,头脑一片空白,怎么都想不起来自己做什么了。”
董妍妍下颌微仰,斜着脸,坐在15楼的飘窗上,背后是密密的楼群,铅灰色的云块和异常压抑的城市。她的脸上布满忧愁,“你觉不觉得现在人活得太压抑了,很没有意思。”
她弓着背,反问我:“有时候我就在想,活着有什么意义呢?”
“你是不是受刺激了?感觉你不大正常。”
“如来佛祖要制我,我能有什么办法?”她耸耸肩,冷漠地说。我不知道怎么回。
让人越来越无法忍受的是,董妍妍虽然没有洁癖,但就是离不开消毒液。哪怕洗内衣都要滴几滴进去搓,导致她的衣服经常白一块花一块的,手上也经常蜕皮。屋子连着阳台,夏天的热风吹进来,扑到脸上热辣辣的,又会忍不住抓挠。时间长了,我发现她的手有点“烂”。房间也和厕所变成了一个味。
“消毒液提神醒脑呢。”董妍妍每次都这样回答我。“我从小闻惯了,现在闻不到就别扭,总觉得房间不干净。”
“你能不能和你屋里的小姑娘商量下啊,大厅里不要洒太多的消毒液。本来房间通风就差,洒了那么多难闻死了。”隔壁的一个年轻女孩几次和我反映。
那个女孩皱着眉头往门里努嘴,“她和一开始来的时候有点不一样了,以前还乐意出来和我们说说话,现在都是门关着,躲在里面怎么敲门都不开的。”
董妍妍吃多了治疗粉刺的激素药,导致月经不调,脸上又开始冒出更密集的粉刺,就这样恶性循环了很久,她买了一堆口罩,出门就戴着。
我搬出去前一晚,她直挺挺地躺在床上,僵硬得像具尸体。只有眼皮微露,无神空洞地望向天花板,嘴一张一合,声音哑哑的听不清。
起初我以为她在自言自语,后来我凑过去仔细听,她是在说:“我是变态,别管我。”
“谁敢说你变态?”我诧异地问她。
“如来佛祖啊。” 她气若游丝地说
“你老说如来佛祖,是谁啊?你妈?”
她没应声。
6
卢也得知我和董妍妍住在一起,三番两次暗示我搬走,他是董妍妍初恋的好朋友。
“董妍妍的黑历史你知道吗?”卢也说着,嘴角浮现了微笑,有些轻蔑的那种。
我还真不知道她的黑历史。
他悠悠地点上一根烟,从前向后抹平了老板头,不疾不徐道:“你知道张峰和她谈了高中两年多吧,毕业张峰就把她蹬了,这小子平时软了吧唧的,这蹬的好啊。”卢也说着拍手称赞道。
谁蹬谁我没在意。
他继续卖关子:“你知道为什么蹬她吗?”
“为什么?这和黑历史有什么关系啊?”我讨厌他一直卖关子。
“因为她不干净。懂什么意思吗?不干净!”耐人寻味的微笑又浮现在他脸上。“我们高中有个小混混喊她出去玩,大家都懂什么意思的,她跟个傻瓜一样就真去了。”他说完仰着脖子干笑两声,手指抖动烟灰跟着落下。
“那个混混高二就辍学了,还没事去学校里游荡,结交了不少异性。董妍妍只是其中最普通的一个,什么狗屁男闺蜜啊,都是骗人的。就她还当真了,屁颠屁颠地跑去唱歌喝酒了。”
据说,这个小混混以醉酒为幌子,占了董妍妍的便宜,董妍妍吃了哑巴亏,也不敢对旁人说。事情本来就这样过去了,但是小混混的女朋友知道了,把董妍妍的“事迹”到处传播,校园里流言蜚语满天飞,张峰没面子,就把她甩了。
后来出事,是因为其他女生也被这个小混混占了便宜,把这件事捅破了,学校老师顺蔓摸瓜地找到了董妍妍。董妍妍一开始抵死不承认,学校老师好说歹说,想让她挺身而出作证,她就是闷头不吭声。
学校的意思是,作证肯定要她本人出面的,不然,还能有什么证据呢?
后来,那个女生家里不知道用了什么法子,让小混混把所有事情招了。学校反而觉得董妍妍品行不端,隐瞒真实情况,更没有遵照安排去作证,就要给她处分。加上她三番五次在教师教学反馈上写下对老师的意见,老师一致同意加重处罚。
“后来事情闹得挺大,董妍妍家里也来学校了,她妈知道董妍妍要被开除了,急得想跳楼,跑到教务主任那里跪了好半天。”
“她妈像个泼妇一样,在学校里就拽她头发拖在地上发疯似地捶打,任凭怎么打,董妍妍就是一言不发。从那以后,谁都远离她。”
后 记
董妍妍送我出去的那天,我拎着两个大包,背着一口袋玉米面。我拒绝了她送的几瓶消毒液。
我们一前一后地走着,什么话都没有说。她带着口罩,露出发肿的双眼。
“什么时候回家,把我叫上一起啊。”
“如来佛祖不给我回去。”她小声地说,像做错事情一样畏缩。
过了一会儿,我客气地说:“今后去我租的那儿玩玩。”
“只要你不嫌弃我就行。”她目光转向别处说道。
我们记不清那些在路上徘徊的日子了,只记得少年时代的理想投身在人海浪潮,如今荡然无存了。